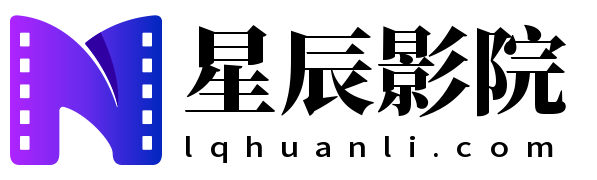刚从瑟堡来的斯蒂芬,加入了巴黎93省圣德尼的“反犯罪特种部队eee。在这里,他遇到了新队友克里斯和瓦达,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街区不同帮派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在一次出警的行动中,局面变得不可控制,而这个事件意外地被一架无人机记录下来,进而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冲突。
演员及所饰演人物
休·杰克曼 饰 冉·阿让
罗素·克劳 饰 沙威
安妮·海瑟薇 饰 芳汀
阿曼达·塞弗里德 饰 柯赛特
艾迪·雷德梅恩 饰 马吕斯·彭眉胥
萨曼莎·巴克斯 饰 爱潘妮
艾伦·特维特 饰 安灼拉
赫莲娜·伯翰·卡特 饰 德纳第夫人
萨莎·拜伦·科恩 饰 德纳第先生
丹尼尔·赫特斯 饰 米里哀主教
详细剧情
故事始于1815年的法国,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而服了19年苦役,终于获得假释。他因前科犯的身份备受歧视,内心充满对社会的仇恨与绝望。善良的米里哀主教收留了他,但他却在夜里偷走了主教的银器。被捕后,主教不仅没有指控他,反而将银烛台也赠予他,谎称是他遗忘的,并嘱托他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主教的宽恕与仁慈深深震撼了冉·阿让,他决定撕毁假释令,改头换面,开始新的人生。
八年后,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市长,成为一名成功的工厂主,深受民众爱戴。在他的工厂里,女工芳汀因私生女的秘密被同事揭发而被解雇。为了抚养寄养在德纳第夫妇家的女儿柯赛特,芳汀被迫卖掉头发、牙齿,最终沦为妓女。在一次冲突中,芳汀被捕,恪守法律的警长沙威要求严惩她,但马德兰市长出面干预,并将她送往医院。沙威对市长的身份产生怀疑,他回想起当年冉·阿让惊人的力量,并写信告发,却被告知真正的“冉·阿让”已被捕。在良心与自保的挣扎中,马德兰市长选择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拯救无辜者。
在医院,垂死的芳汀从冉·阿让那里得到了会亲自接回柯赛特的承诺。沙威赶到逮捕冉·阿让,后者在芳汀死后短暂逃脱,前往德纳第夫妇的旅店。德纳第夫妇是贪婪无情的客店老板,将柯赛特当作女奴般虐待。冉·阿让用重金赎走了柯赛特,两人在巴黎的隐居生活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父女温情。
数年后,在巴黎,长大成人的柯赛特与热血青年马吕斯·彭眉胥一见钟情。马吕斯是ABC之友社的成员,这是一群旨在推翻腐朽王权的革命青年。与此同时,一直追捕冉·阿让的沙威也调任至巴黎。德纳第夫妇因破产来到巴黎,继续行骗。在街头,对马吕斯怀有单相思的贫苦少女爱潘妮,虽然心中痛苦,但还是帮助马吕斯和柯赛特传递爱意,成全了他们。
1832年巴黎六月起义爆发,ABC之友社在街头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殊死搏斗。冉·阿让为了守护心爱的女儿柯赛特所爱的人马吕斯,也来到了街垒。在混战中,爱潘妮为保护马吕斯中弹,死在了他的怀中。冉·阿让在街垒中发现了前来侦察的沙威,但他在有机会杀死沙威时,却选择放走了他,再次践行了主教的仁慈。
革命最终失败,街垒被攻破。冉·阿让从战场上救出昏迷的马吕斯,背负他闯入巴黎复杂如迷宫的下水道。在黑暗与绝望中,他几乎放弃,但最终凭借着对柯赛特的爱与承诺坚持了下来。在下水道出口,他们遇到了等候在此的沙威和正在勒索的马吕斯的“救命恩人”——德纳第先生。沙威亲眼目睹冉·阿让的善举,其一生坚守的“法律不容宽恕”的信仰彻底崩塌。他在留下一张字条后,投塞纳河自尽。
马吕斯康复后与柯赛特结婚。德纳第夫妇试图以“街垒杀手”的真相向马吕斯敲诈冉·阿让,却歪打正着,反而向马吕斯揭示了冉·阿让才是他的救命恩人,以及自己曾经的种种恶行。马吕斯和柯赛特赶到冉·阿让的身边,此时他已年老体衰,生命垂危。在柯赛特的陪伴下,回溯自己充满救赎与爱的一生后,冉·阿让在幻想中见到了芳汀和爱潘妮的灵魂,安详地在主教的指引下离世。
影评
《悲惨世界》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音乐剧之一,其改编成电影的呼声由来已久。当汤姆·霍伯接下这一烫手山芋时,他所面对的不仅是亿万观众的期待,更是一个几乎被视为完美的艺术范本。最终的电影成品,是一次雄心勃勃、充满争议但又难以否认其情感震撼力的改编。它并非一部无懈可击的杰作,却是一部在艺术选择上极为勇敢、在情感表达上臻于化境的银幕史诗。
影片最核心、也最具颠覆性的导演决策,无疑是现场同步演唱的录制方式。传统电影音乐剧采用先录音、再拍摄、后对口型的方式,以求得声音的完美无瑕。而霍伯反其道而行之,让演员们在拍摄现场戴上微型耳麦,根据现场钢琴伴奏直接演唱。这一选择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赋予了表演前所未有的“即时性”和“真实感”。演员们不必再分心于对准口型,而是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情绪的起伏中。休·杰克曼在冉·阿让假释时唱出的《何事西行》,歌声中的疲惫、挣扎与愤懑,是通过颤抖的气息和随时可能破音的边缘感传递出来的,这是录音棚里打磨得再精致的歌声也无法比拟的。安妮·海瑟薇的《我曾有梦》更是这一方式的集大成者,镜头以一个令人窒息的特写直面她的脆弱与绝望,每一次抽泣、每一次声嘶力竭都化为原始的情感冲击,直接刺入观众的心脏。这种真实感,让音乐不再是华丽的间奏,而成为了角色内心独白最赤裸的延伸。
但另一方面,现场演唱的代价是牺牲了部分声乐的完美性。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罗素·克劳饰演的沙威。克劳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他用坚毅、内敛甚至有些木讷的方式,诠释了沙威这一法律的死忠信徒,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而是一个被非黑即白的信念所困的悲剧人物。然而,他的唱功显然无法应对原剧中那些需要强大共鸣和爆发力的曲目。他的演唱时常显得吃力、音准不稳,缺乏一种作为“信念化身”应有的压迫感。这成为了影片最大的争议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唱”与“演”的不平衡,似乎也暗合了沙威角色的内在矛盾——一个僵化的灵魂试图用歌声表达复杂的情感,其本身就是一种失调。
在视觉风格上,霍伯延续了他《国王的演讲》后的偏好,但又将其推向了极致。影片的画幅比极为宽阔,但导演却偏爱使用大量的特写镜头,将人物的痛苦、喜悦、挣扎无限放大,与影片宏大史诗的背景形成一种奇异的张力。这种“以小见大”的处理方式,让观众始终与角色的情感保持零距离,无论是冉·阿让在下水道中的绝望,还是马吕斯在战友牺牲后的悲痛,都仿佛是身临其境的体验。美术与服装设计精准地复现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风貌,从泥泞的街道到华丽的舞会,每一帧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影片的演员阵容,除了海瑟薇的封后级表演和杰克曼呕心沥血的全情投入外,配角同样熠熠生辉。萨曼莎·巴克斯将舞台剧版爱潘妮的精髓完美移植到银幕上,她的《独自彷徨》情真意切,成为全片最催泪的段落之一。艾迪·雷德梅恩的马吕斯,唱腔带有独特的忧郁气质,将一个年轻理想主义者的浪漫与脆弱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赫莲娜·伯翰·卡特和萨莎·拜伦·科恩饰演的德纳第夫妇,则为这部基调沉重的影片注入了必要的黑色幽默,他们的《主人之家》是片中难得的轻松时刻,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物的投机与麻木。
从主题深度上看,电影成功地抓住了原著与音乐剧的核心——救赎、爱与变革。冉·阿让的一生,是从法律之恶走向神圣之善的旅程,米里哀主教的银烛台贯穿始终,象征着信仰与宽恕的传承。沙威的自杀,则是对僵化秩序的彻底否定。而围绕马吕斯的青年革命线,则探讨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与幻灭,为个人命运的悲歌增添了一层宏大的历史背景。
总而言之,《悲惨世界》(2012)是一次充满魄力的改编。它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真诚,试图将舞台艺术的感染力与电影媒介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它或许在声乐平衡上存在瑕疵,在导演风格上有人为嫌其用力过猛,但它在情感传达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它让观众不仅仅是在“看”一个故事,更是在“感受”一段历史,体验灵魂在苦难中挣扎、升华的痛苦与荣光。这便是它作为一部电影改编作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问答清单
1. 问:电影《悲惨世界》在制作技术上最大的创新是什么?这一创新带来了什么影响?
答: 最大的创新是采用了“现场同步演唱”的录制方式,即演员在拍摄现场直接演唱,而非先录音再对口型。其积极影响是赋予了表演极大的真实感和即时性,演员的情绪和声音融为一体,情感表达更加原始、震撼。其消极影响是牺牲了部分声乐技巧的完美性,一些唱功相对较弱的演员(如罗素·克劳)的表现因此受到争议。
2. 问:沙威这个角色最终的自杀,象征着什么?
答: 沙威的自杀象征着其毕生坚守的“非黑即白”的法律信念体系的彻底崩溃。当冉·阿让——一个他眼中的罪犯——两次对他施以仁慈(在街垒放他和他救了马吕斯)时,他无法将这种善行纳入自己僵硬的道德框架中,最终选择了以死亡来逃避这个无法理解的、充满矛盾与宽恕的世界。
3. 问:除了主角冉·阿让,哪位角色的表演被认为是影片的情感高光?为什么?
答: 是安妮·海瑟薇饰演的芳汀。尤其是在她演唱《我曾有梦》的片段中,导演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特写镜头捕捉了她最脆弱、最绝望的一面。她的表演融合了精湛的演技和充满情感撕裂感的歌声,将一个母亲被社会抛弃、希望彻底破灭的悲剧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4. 问:爱潘妮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 爱潘妮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马吕斯的悲剧性陪衬,其得不到回应的爱深化了故事的悲剧色彩。她也是连接马吕斯和柯赛特的纽带,是她促成了两人的相遇。最后,她的牺牲精神与德纳第夫妇的自私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人性中即使在最困苦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的光辉。
5. 问:电影的背景设定在1832年巴黎六月起义,而不是更为人熟知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选择有何深意?
答: 这一选择让故事的核心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人化的情感与理想主义。1832年起义是一场规模较小且迅速失败的、主要由学生和工人领导的起义。它的失败属性,更贴合影片中青年们的激情、幻灭与牺牲的浪漫悲剧感,使得马吕斯等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结合更为紧密和悲壮。
6. 问:德纳第夫妇在影片中的功能仅仅是喜剧调剂吗?
答: 不完全是。除了提供必要的喜剧缓和紧张的气氛外,德纳第夫妇更是维多利亚时代(此处指法国同时代)社会底层人性黑暗面的集中体现。他们代表了极致的自私、贪婪和投机主义,是那个社会道德沦丧的产物。他们在结尾处的讹诈行为,最终反而证实了冉·阿让的善良,起到了反衬主角光辉的作用。
7. 问: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光”的意象(如主教的银烛台)有何象征意义?
答: “光”象征着希望、救赎、神性与爱。主教的银烛台是第一道“光”,它照亮了冉·阿让黑暗的内心,开启了其救赎之路。此后,烛台作为实体贯穿全剧,而柯赛特也被称为冉·阿让生命中的“光”。与之相对,“黑暗”则代表了监狱、压迫、绝望(如下水道)。
8. 问:导演汤姆·霍伯在影片的视觉构图上有什么显著特点?
答: 他偏爱使用广角镜头配合大量的面部特写。这种组合方式在营造宏大史诗感的同时,又能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与角色产生极强的情感共鸣。画面的倾斜角度和紧凑的构图也时常用来表现人物内心的不安与社会环境的动荡。
9. 问:如何评价罗素·克劳饰演的沙威这一角色?
答: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表演。从表演上看,克劳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刻板、坚毅、内心充满矛盾的法律执行者。但从音乐剧的角度看,他的演唱能力被普遍认为无法胜任角色对声乐的要求,缺乏力量和层次感,使得这个角色的威慑力和内在张力有所削弱。
10. 问:冉·阿让这个角色的人物弧光是怎样的?
答: 冉·阿让的人物弧光是一个从“恨”到“爱”,从“兽性”到“神性”的完整转变过程。他从一个被社会不公扭曲、心中充满仇恨的苦役犯,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选择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他用一生去践行承诺、保护弱者、施以仁爱,最终从一个法律的“罪人”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圣人”,完成了灵魂的升华。
展开